          | |
| 翻墙 | 三退 | 诉江 | 中共卖国 | 贪腐淫乱 | 窜改历史 | 党魁画皮 | 中共间谍 | 破坏传统 | 恶贯满盈 | 人权 | 迫害 | 期刊 | 伪火 社论 | 问答 | 剖析 | 两岸比对 | 各国褒奖 | 民众声援 | 难忘记忆 | 海外弘传 | 万人上访 | 平台首页 | 支持 | 真相 | 圣缘 | 神韵 | |
|
【大纪元2021年09月02日讯】 自1963年8月底起,我在“东海东,玉山下”的台北市建国中学(以下简称为建中)混了九个月左右,那是我高中时期的最后一年。至于“东海东,玉山下”又是什么“碗糕”?我想所有建中毕业生都会记得的,那是咱们校歌的头两句。 我自幼成长于高雄县凤山镇(现今的高雄市凤山区),所以原先读的是省立高雄中学(以下简称雄中)。当然,台湾南部绝非“文化落后”地区,特别是位于高雄市的雄中与位于台南市的南一中,他们的毕业生在大学联招之录取比率都极高,只是建中的“名气”好像更高一些,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之下,我经转学考试进入建中,是1963年被录取进入高三就读的十名插班生之一。  图:1963年我就读于建中高三6班时期之“校服照”。(作者提供) 图:1963年我就读于建中高三6班时期之“校服照”。(作者提供)
雄中校区离火车站很近,校园北端与铁道相邻,刚离站的火车会鸣笛加速,噪音很大,最靠近铁道的那排教室,声音大到会掩盖老师的授课声。不过久而久之,大家也都习以为常,老师大概也乐于有约半分钟的Break time吧。 建中校区则得天独厚,与环境优美的“南海学园”相邻,园区内有仿北京天坛而建的科学馆,配以馆旁植物园内的荷塘(或许是莲池,事隔久远,我记不得了),还有当时台湾最大的中央图书馆,与一栋美轮美奂的宫殿式建筑物──历史博物馆。刚到台北时,这“南海学园”的景色,是让我这南部来的“乡巴佬”十分惊艳的。 在建校历史上,建中、雄中与南一中等各地之“标竿”中学,大约都是在1910年左右的日殖时代创办的,它们也全是台湾各地的“一中”之一,是只供日本殖民者之子女念书的专属中学。被统治的台湾人之子女,只能在校舍、设施与师质皆属二流或更糟的“二中”(甚至于三、四中)就读,日殖时代之不公不义,莫此为甚。 在此也附带提及,日殖时代只有台中的“一中”是全台唯一兼收极少数台湾人子弟的中学,这是因为“中一中”原址是台湾人自己集资所办的学校,遭殖民者强制征收校舍且改名为“一中”后,不得不允许少数创办人之子女留在原校就读之故。 现在身在台湾的两千三百多万居民,有必要牢记一些当年日本殖民者欺压台湾人的残酷事实。根据日殖总督府自己公布的历史纪录,当年唯一的全科大学(就是现今之国立台湾大学),有三十三年之久是禁止台湾人入学的,直到1928年改制为台北帝国大学后,才逐渐开放让台湾学生就读,统计自1928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17年间,堂堂一个经常维持有千余学子的台湾首学,其台湾籍学生之人数仅从1928年的6人,增加到1944年的60人,而这些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还在学的60位台湾籍学生中,有近五十位是被日寇指定去学医的,那是因为二次大战末期,在各地征战之日军伤亡极重,急需战地医护人员,医学院只是配合着日本军阀之侵略政策去招收台湾籍学生(仍然是二等公民)而已。 在简介两校之校史后,请敞开心怀看看我对这两所学校的感受罢。我无意在此判定“建中”与“雄中”之优劣,何况当时的雄中校长王家骥,与建中校长贺翊新,都是全国知名度极高,也备受学生爱戴与尊崇的教育家,我能比较的,只是这一南一北两所“标竿”学校的校风而已。 简单地说,“雄中”校风趋向“保守”,相较之下,“建中”则是相当“自由开放”的。您看,建中校歌中就有这么一句“春风吹放自由花”,简直像是在鼓励学生去“搞怪”。而雄中在校歌中则搬出“礼义廉耻,是所遵从”作歌词,八成是要求学生们循规蹈矩,最好给我“安分”一点。 想要比较这两所中学的“校风”,还有个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比较它们的“午休时间”之活动。 在雄中,午休时间是有门禁的,学生们必须留在校园内,每一班的值日学生(2至4位)在上午第四节课上到一半时,班长会提醒他们提前几分钟去厨房,把一早就送去加热的五十个左右便当抬回教室,这样子学生们在午休时才有热便当可吃。 当然,没有带便当的同学,是可以在校门口(不可以出校门)向兜售食物的小贩购买便当的。 那么吃完午餐以后呢?雄中的学生至少有一半以上会自动自发地以臂作枕,趴在书桌上“打个盹”,主要原因是,没有什么“午间活动”。 相较之下,建中的午休时间则是完全开放的,学生们可以自由外出,吃自备的便当也好,在外面小吃摊(店)点餐也好,只要你下午一点整准时回教室上课,所有午间活动都没有管束,我的午休时间通常是会出校门用餐的。 既然在“午休时间”学生们的活动完全自由,我这南部来的“乡巴佬”生怕被同学视为“异类”,所以有时也会“入境随俗”地跟着他们一起“搞怪”。当然,我所谓的“搞怪”,也绝不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只是行为约略超过了校规所釐定的范围,譬如说,结伙去弹子房打撞球之类的“坏事”。 现在回想起来,打撞球真的不是什么天大的“坏事”,之所以被“禁打”的原因,或许是与那些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招徕顾客的“计分小姐”有关。有些顾客(非学生)来“消费”时,会刻意付钱找计分小姐“陪打”,她们为赚取小费,也就乐于执杆应付。但若是有客人“撞”翁之意不在“球”,与计分小姐纠缠不清时,就可能会产生麻烦。 在弹子房生意清淡时,常见计分小姐们乒乒乓乓地在“练球技”,熟能生巧,有些计分小姐也的确是身手不凡呢。 位于南海路的建中校门不远(约五分钟脚程),有一条与南海路垂直交会的南昌路,那儿就有一间弹子房,而且是具有特殊“逃生设备”的弹子房,好像是专门给咱们建中学生而设的,所以我们这群来“搞怪”的学生都“趋之若鹜”。 那间弹子房从街面上看起来,只有四座弹子台,其实后面还有个门,门后有楼梯,楼上有一间较小的店面,摆了两座弹子台,我们建中学生怕“搞怪”时被巡逻的教官逮到,平常都“躲”在楼上打撞球。通往楼上的那个门有锁,楼上有“客人”在时就上锁。 楼下的计分小姐若是见到建中军训教官来“突袭”检查,会拨一个隐藏的按钮,启动楼上的红灯,计分小姐会机警地将我们建中学生统统赶进一间有反锁的储藏室里,那储藏室就是我们的“逃生间”啦。 我读建中的那一年,好像这“逃生间”尚未被军训教官识破,我也不是经常去打弹子的,只是实际“演习”过,得如何“敏捷地”在几秒钟之内躲进“逃生间”。后来听说这“逃生间”遭人密告,弹子房只好将二楼关闭,不过那时我已进入台南成功大学,“名正言顺”地在校门口的“大千弹子房”,练就一身“武艺”。 当时,国联电影公司的摄影棚就在校门斜对面的南海路上,古装片“七仙女”正在摄影棚内摄制中,李翰祥是该片之导演,女主角就是当年火红的江青(这艺名倒是与毛大王的压寨夫人一样)。摄影棚虽未对外开放,但是也没有赶走站在棚外之旁观者,由于“站位”有限,捷足者先登。有好几次我想要在午休期间一睹“仙女”们之倩影,都因观众(几乎全是建中学生)太拥挤而放弃。 所以放学后,在观众不太多时,我曾去当场看了几次。但是同一场景常遭李大导演NG,重复拍摄的过程让我看得有点儿嫌烦。还有,众“仙女”们的化妆也嫌太浓了些,浓得像平剧里的花旦,愈看愈不够“仙”,看过两、三次之后,我也就兴趣大减。 这“七仙女”电影当年还闹了个“双胞案”,香港邵氏的“七仙女”原本也是李翰祥导演的,李大导不知为何与邵逸夫翻了脸,邵氏的“七仙女”已拍了一大半,李大导却转移阵地到台湾,用同一个剧本拍同名电影。邵氏的“七仙女”因为是由当年红透半边天的凌波主演(反串男主角董永),所以在票房上远远超过了国联的版本。日后国联的“七仙女”在台湾上映时,我居然还去戏院连看了两遍,特意寻找那“似曾相识”的场景,现在想起来确实是有点儿闲极无聊,对罢? “午休时间”也是建中鼓号乐队的练习时间,地点就在名闻遐迩的“红楼”宽敞玄关中,当年建中参加全省高中鼓号乐队比赛之曲目,是我自幼就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之一,维帝(Verdi)所作之名歌剧阿伊达(Aida)中,那雄壮悦耳的“凯旋进行曲”(Triumphal March)。原本应该是由交响乐团演奏的名曲,在建中乐队的鼓号声中(缺弦乐器),其悠扬旋律依然让我“振奋”不已。 那一年的全省高中鼓号乐队比赛,建中就是以此曲勇夺全省中学组冠军的。 如果中学生“打撞球”是“坏事”之一,“打橄榄球”则正好相反,它是建中学生引以为傲的“镇校之宝”,不但校方积极鼓励,也是所有的课外活动中,最让我欣羡的球类运动。 或许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橄榄球,所以那“斗牛”式的打法让我觉得十分新奇,经常站在操场边看得出神。后来到了美国,入境随俗地迷上了另类的橄榄球赛(打球之方式迥然不同),那就是被美国人“霸道”地称之为Football的美式足球American Football。 您看,明明使用的是橄榄球,在美国却被冠以足球之名,然后将世界各国公认,经国际足球联盟(FIFA)确认的名字Football,硬生生地改名为Soccer,然后还强迫地将我在建中时看到的“橄榄球”比赛名之为Rugby,这不是“霸道”又是什么? 你想要在建中被选为橄榄球校队球员还很不简单,除了要具备强健的体魄之外,功课还得维持在“前段班”中的“前段”才行,所以校队球员们都是班上成绩优秀的学生,日后也都进入了比较“理想”的大学或是科系。我们班上只有一位橄榄球校队球员,他就是后来考上台北医学院医科的江明哲,听说他日后也成为实力坚强的北医橄榄球队主将之一。 我读建中的那一年,咱们的橄榄球校队拿到台湾光复后的第十八座冠军杯,而且还是连续十八届呢。后来我在台南市的成功大学就读时(忘记是那一年),全省中学橄榄球赛的冠军居然第一次易主,被私立长荣中学(也位于台南市)夺得,害得我“心有戚戚”了好几天呢! 那1963年的下半年,国内外都出了些大新闻。在国际上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美国甘迺迪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遇刺的消息。但是在台湾的社会上,这“甘迺迪遇刺”事件,其轰动之程度还远不如同一时段,那周鸿庆在东京“投奔自由”后,遭日本政府强制遣返中国大陆所引起的“群情激愤”呢。 之所以在此特别提及“周鸿庆遭遣返”事件,是因为有些“抗议活动”,有建中学生积极参与,而且确实是“自动自发”的,没人在幕后指点。 话说这周鸿庆“投奔自由”后遭强制遣返事件发生时,中华民国与日本尚有正式的“大使级”邦交,当时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早已与中共在暗中眉来眼去地勾搭,例如鼓动日本油压机械工业协会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日本参访等。 一位在中共油压机械工业代表团里担任翻译的周鸿庆,于全团返国前夕之10月7日,脱团“投奔自由”,因人生地不熟而误入苏联大使馆,被苏联大使馆移交给日本政府相关单位羁押,不但没了“自由”,最后还于1964年元月9日,遭日本政府雇用商船“玄海丸”(大概当时两地尚未直通航机)强制遣返大陆。由于担心中华民国可能会派舰在公海拦截,日本海军居然还派了艘军舰,一路“护送”玄海丸由大阪驶到大连港。 周鸿庆投奔自由遭日本遣返大陆事件之详细经过,网路上已有不少文章,在此不多着墨,不过我得要提醒你,有几篇文章强调他是“自动自发”回大陆的,但那是恶名昭彰,最擅扯谎的中共国务院直辖的“广电总局”瞎掰的文章。君不见,周鸿庆回到大陆后就“失踪”啦,在国外“丢”了毛记政权如此大的“脸”,他还会有好下场吗?后来居然有一位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记者,想要去大陆访问“坚决要重返祖国”的周鸿庆,毛共当局无法交代,只好一口回绝。以毛记政权之残暴本质,我估计周鸿庆被遣返后,最多存活了不到十天。 此时台湾全岛舆情激愤,元月14日(周鸿庆于12日“安抵”大连),数千群众齐聚日本驻华大使馆前抗议,当场若是没有军警拦阻,那使馆早就被“攻陷”啦! 数日后的午夜时分,日本航空公司台北营业处的玻璃大门遭到砖击,碎片满地,现场照片也上了报纸社会版的头条,“暴徒”则消遥法外。事隔一甲子后,我不妨在这儿爆个料,那是几位当时就读建中高三的学生干的好事。不过请看倌们别过度地“举一反三”,我谢某人可不是那“暴徒”之一。 那又如何证明我本人没有参与“施暴”呢?非常简单,看过我写的“浮生六记所衍生出来的故事”一文之读者,该记得我读建中那年,被我父亲“看管”甚严,与他老人家同住在位于当时还是台北市郊区的大直,一栋在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区内的军官宿舍里。再加上三军联大有特殊门禁,我半夜溜出军官宿舍,穿过戒备森严的校门去干“坏事”的可能性是“零”。 哦,不就是个军校校门嘛,干嘛搞得那么神秘兮兮地,那是因为三军联大的前、后门之间的通道,是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也是通往被列为高度机密之“衡山指挥所”的主要道路,三军联大的后门与指挥所入口(当然,指挥所之入口绝不止一个)的直线距离,最多不超过五十公尺,其戒备岂止是用“森严”两字可轻易描述的。 所以,我的确没有参与砸日航营业处玻璃门的“壮举”,充其量只算是“知详情而未报”。至于是些什么人干的,我只能说,那一届的建中高三学生超过900名,是其中的几位热血青年干的。不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倒是曾经滔滔地告诉过当时与我住在同一间卧室的父亲,他老人家瞪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完后,面容严肃地命我“封嘴”。 我就这样“封嘴”封了近一甲子,现在讲出来后总算是舒了一口气。 “玲姨”是彭绣谷,辈份上高我一辈,是我母亲的小表妹,但年龄上只长我半岁而已。她的母亲范新琼是我母亲的亲姨妈,不但与我血脉相连,而且还是位非常疼爱我的姨外婆。范新琼是早年“勤工俭学”留学法国的留学生之一,她老人家是画家,我以前写过一些她的故事。“玲姨”的哥哥,就是前台北荣总的院长彭芳谷医师。 与小名“阿玲”的玲姨第一次相遇,是1949年在九龙牛池湾的难民营里,她与家人也是因逃避赤祸而赴港,所以玲姨与我虽然差了一个辈份,但确曾是幼时的玩伴。我的姨外公彭襄(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文学博士)在留学法国时,与一众左倾中国留学生是时相往来的朋友。避难九龙其间(前后约三、四年),他们都曾力劝姨外公回大陆“报效祖国”,但姨外公不为所动,反而与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另两位留法时期好友,时任国府司法行政部长的郑彦棻,与立法院长张道藩等联络上,举家来到台湾“共赴国难”。日后他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任法文教授,家住台北新店,我则随同父母住在高雄凤山,玲姨与我就这样“一北一南”地分别长大。 顺便一提,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中的“中法”两字所代表的,只是“勤工俭学”的里昂大学中国留学生而已,不是另外一所特殊学校,所有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没有一堂课不是在里昂大学上的。 转学去台北读建中的那一年,我为大专联招的升学考试而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偶尔还是会随父亲去新店亲戚那儿走走,因为除了姨外婆住在新店七张的十二张路之外,我的范表舅(母亲的表弟范如仲)也在七张的“台湾三育书院”任教,两家相隔很近,去一次可拜访两家。 玲姨嘴甜,我父亲谢肇齐是她口中的“齐哥”,我母亲余莉丽则是她的“莉姐”,我父母亲都被她那张甜嘴“驯”得服服贴贴,好喜欢她。中国传统家庭“长幼有序”,可是要我去唤只长我半岁而已的儿时玩伴为“阿姨”,我还是叫不出口,所以就执拗地只肯喊她的小名“阿玲”。  图:1964年,19岁的玲姨摄于台北新店自家后院。(作者提供) 图:1964年,19岁的玲姨摄于台北新店自家后院。(作者提供)
那年玲姨是政治大学外语系的“新鲜人”,当年在台湾,由中学生“升级”为大学生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更何况“政大”也是“文组”考生心目中的顶尖大学之一。总而言之,那正是玲姨“春风得意”之时,让我这中学生欣羡不已。不过才三、四个月前,她也就是个中学生而已,八成与我一般,被大专联考这人生“关卡”,煎熬得寝食难安,因为即使读的是“明星”高中,也不是保证你一定可以考进理想学校与科系的。 那天,玲姨本来就已约好她中学时期(二女中)的两位同学,一道去西门町的“红楼”看场电影,见我皱着眉,一付心神不宁的样子,乃向她的“齐哥”建议,让她带我一起出去看场电影轻松一下。我父亲居然同意,因为当天下午,他得陪我的姨外婆打八圈家庭麻将,本来就担心我会闲极无聊,无法打发时间,不但如此,还塞给玲姨几张票子,讲明这场电影是由他请客。 由于气象预报是“晴时阵雨”,姨外婆交代我俩得带伞出门,玲姨顺手拿起一把时髦的折叠伞,两人兴冲冲地出门奔赴公车站。 到了台北公车总站,我俩都是体力充沛的“大孩子”,决定沿中华商场(现在早已拆除)走向西门町。走着走着,果然下起雨来,而且还不算太小,我撑开伞一看,不禁当场气结,那根本是把给姑娘遮阳用的小花伞,由于那伞实在太袖珍,我俩挤在伞下还是各淋湿了一半,我一路气急败坏地嘟哝着玲姨,她脾气真好,没顶我半句,只尴尬地抿了抿嘴。 到了西门町后,两人在约定见面的一间冰淇淋店门口傻等,见时间尚早,就进店叫了两客霜淇淋,站在拥挤的骑楼下边吃边等人。才吃了两、三口,突见两个女孩子蹑手蹑脚地走到玲姨背后,我还没来得及警告她,两人就同步大声喊“彭绣谷”!吓得她差点把手中的霜淇淋掉落地上。 “难怪前阵子打电话找你出来玩,你都说没空,原来??”她俩上下打量着我。 “哼!你未免太不够意思啦!既然要带男朋友来,也不事先通知一下??”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玲姨被呛得愣在当场。 “谁说我是她男朋友,她是我的??呃??”我抢着回答,但是要在公开场合叫她一声“阿姨”,总还是有点儿“不甘心 ”。 “误会一场,我是他的阿姨。”玲姨终于开口。 “呵?你想骗谁?你怎从没提过你有这么大的一个晚辈?” “他一直住在南部,上个月才转学到建中读高三。” “个头儿这么大,才中学生吗?刚才看到有‘人’替你打伞,我们都不敢认你啦。”话说得酸溜溜地,两人显然已盯梢了好一阵子。 “那??那又怎样?我们只有这么一把伞。”玲姨呛了回去。 “她真地是我妈的表妹,我还有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呢,在辈份上我们都低她一辈。”我耐心地解释。 “好罢!不过既然有个‘男生’在,这场电影可是得援例由‘男生’请客的。”两人一付不肯罢休的样子。 父亲给我俩的零用钱是放在玲姨那儿,我无权做主。 “嗳,好吧,那你去买四张学生票。”玲姨无奈地掏钱给我,我心中还觉得好笑,她这是在慷 “齐哥”之慨。不过还好,西门町“红楼”剧场的学生票特别便宜。 “等等,刚才不是讲好由‘男生’请客的吗?”见是玲姨掏钱,这两位女生还不肯罢休。 “那儿能要我‘晚辈’掏腰包。”玲姨扬起头,一边掏钱出来,一边故作正经地嚷嚷。我咬紧嘴唇,怕当场笑出来就“破功”啦。 自此以后,玲姨的好几位“姐儿们”都知道有我这“晚辈”之存在,也与她们同去“红楼”戏院看过好几场电影,我常遭她们当“晚辈”支来使去,心有不甘,乃亟思“报复”。 有一次我与几位建中同学一起翘课,去“红楼”看了一部片名为“惊魂记”的恐怖片(Scream of Fear),导演(英国名导Seth Holt)之手法绝不下于希区考克,剧情令人毛骨悚然,观众中不断地传出阵阵惊叫声,好像都是女性的声音。 看完电影我心生一计,周末时约玲姨与她的“姐儿们”同去看这部电影,我已知晓电影情节,所以只顾借着银幕的微弱反光,偷看众“姐儿们”的惊吓表情,电影情节愈惊悚,我愈笑得乐不可支,终于被“姐儿们”之一看出我在幸灾乐祸。 散场后我遭“压倒性”地责怪,被众“姐儿们”逼着掏尽腰包买“霜淇淋”给她们“压惊”,要不是玲姨帮忙凑了几个零头,我连回大直的公车钱都没啦。 不过她们这“霜淇淋”也不是白吃的,这几位“姐儿们”后来都帮过我忙,至于帮的是什么忙,且请众看倌继续读下去。 转眼间,这已是近一甲子前的往事。玲姨大学毕业后,在位于台北新店的台湾电子公司(主要是研制电视机之映像管)任职时,结识美籍电子工程师海国栋(Bill Hagadorn),他们于1968年结婚时,我正在马祖服兵役,没能参加他俩婚礼,婚后不久他们就搬到美国,住在田纳西州东部的一个小城Morristown。 1972年我在美国就业的第一份差事,是位于田纳西州西部的另一个小城Milan。田纳西州州形东西狭长,这两个小镇,相距居然有300英里左右,见面不易。 1974年春,我已经接到去德州达拉斯工作之聘书,心想若再不与他们见次面,一旦离开田纳西州后就更难了,乃开了近六小时车(那阵子高速公路行车的速率限制在55 mph),与他俩在美国第一次相聚,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玲姨。 七十年代末,他们举家西迁至Oregon州Portland市。1984年某日,玲姨遇车祸逝世,享寿不到四十,车祸原因是对方酒驾,高速撞到正在步行通过斑马线的玲姨,真的是祸从天降。 在赶赴Portland参加玲姨葬礼的飞机上,我脑海里尽是些往日情节,“各淋湿了一半的那场雨”,“西门町的霜淇淋”,“电影院里的恶作剧”,“在美国重逢的欢愉”。它们就像跑马灯似的“转个不停”,也让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个不停”。如今,每念及这近四十年前之惨事,仍令我扼腕唏嘘不已。 北部中学生名堂忒多,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准备大专联考上已经是够心力交瘁的,居然还得“照惯例”,搞个什么“毕业舞会”,而且还是由各毕业班“自筹自办”,不像现在的美国高中应届毕业生的Prom舞会,原则上是由校方主办的。六十年前台湾的高中毕业班还没这“规矩”,想要搞毕业舞会,得“自食其力”。 办“毕业舞会”是需要租场地与音响的,没钞票就不能办事,赚钱点子当然不少,也都是建中的“前辈们”传下来的,其中被我们认为可行的,是租用“廉价”的台北中山堂,办两场“电影欣赏会”赚钱,记忆中好像每位同学都得负责“推销”至少二十张票以上,否则自己得要“吞下去”。两部电影的片名分别是“手提箱女郎”与“蓬门今始为君开”,前者是得了1961年欧洲影展首奖的意大利片,后者是得了1953年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喜剧片,虽然名气都不算小,但当我们租来时,它们都已是在第三轮戏院放映过不少次的老片子啦。 想要推销这么多老电影的票,只有靠“卖人情”,而我的“哥儿们”与人脉之“基本盘”远在高雄,眼看就得自己“吞”下新台币四十元(每张票仅两元)之际,脑袋里灵光一闪,想到了玲姨的众“姐儿们”。承她们帮忙,各自“勉强”认购了几张,再加上当时在北一女高三良班(北一女以温、良、恭、俭、让为班名)就读的“绛妹”也帮忙推销了好几张,最后只剩一张而已,就被我留下来当纪念品啦。  图:这是当年我们高三六班办的电影欣赏会票根。(作者提供) 图:这是当年我们高三六班办的电影欣赏会票根。(作者提供)
“绛妹”是我的堂妹谢绛光,她的尊翁是早年留日习农的谢鸣轲先生(长期担任屏东农林改良场场长),鸣轲伯不但与我父亲是同乡同宗(共一位四世祖先),两人还是中学住宿舍时的上下铺同学,所以两家当年在台湾之交往十分密切。绛妹日后留学美国,是位双科博士(营养学与医学博士),一生成就非凡,她更是我俩的共同家乡──福建武平,谢氏家族之光,可惜于盛年病逝,也是我生平的憾事之一。 至于那“毕业舞会”办得如何啦?呃,好像还不错,不过说来你或许不相信,我根本就没参加,因为当时我随同父亲,住在位于大直“三军联大”校区内的军官宿舍里,那儿门禁森严,我这非军人的“小朋友”,在夜间是进出不了校门的(除非我与我父亲同行)。 我自青少年时期起就开始“集邮”,照台湾邮政总局的宣传广告,“集邮”是“益智,怡情,储财”的最佳“嗜好”,所以我奉行多年。大概是受“集邮”之影响,所以我连带也有“搜集票根”的习惯。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好习惯”,这“搜集票根”的习惯让我在“爬格子”时,增添了一堆题材,也让读者们可以“见图识文”,是吧? 手头珍藏了九场1964年“四国五强”篮球赛的票根,那一叠票根所代表的,不只是我当年有幸现场目睹激烈国际球赛之“自傲”,也充满了点点滴滴的“父爱”,是我年轻时不懂得体会的父亲“亲子之情”,更是我日暮之年,感念亲恩的媒触。  图:这是妥藏了一甲子的几张“四国五强”篮球赛票根之一,它表达了我对浓浓父爱之珍惜。(作者提供) 图:这是妥藏了一甲子的几张“四国五强”篮球赛票根之一,它表达了我对浓浓父爱之珍惜。(作者提供)
话说我11岁到18岁之间,父亲工作的军事单位在台北,与我们在高雄县凤山镇的眷舍是一南一北,父亲只得两地奔波,而且在家的时间少,原则上每个月只有一个长周末(周四至周日)而已,以民国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台湾铁道运输工具而言,两地的“距离”至少是六小时。所以父亲即使是乘坐当年以“飞快车”为名的快车回家渡长周末,感觉上也好像总是“来去匆匆”似的。 我这辈子非常幸运,从双亲那儿得到了“大量”的爱,母亲的爱偏向于“溺爱”,是生活上与物质上的照顾,父亲给予的爱虽然也相似,但方式有异,甚至还加上了“精神上”的鼓舞。 打个比方吧,我大学毕业后得服一年兵役,当母亲得知服役地点是马祖列岛中,一个面积仅约两平方公里的“离岛中之离岛”──东犬岛时,当场吓得掉眼泪,父亲则淡然处之,认为那是花钱都买不到的“男孩成长时应有之历练”,两人还为此而大吵了一架。我则自始至终赞同父亲的立场,讲句玩笑话吧,我要是没有这危机四伏的“外岛历练”,那儿写得出那篇自鸣得意的文章──“服兵役的那一年”呢。 父亲想必是意图弥补他在我成长时期之“缺席”,所以与他老人家同住一室的这一年,在督促我准备大专联考之际,也尽量提供我一些“父子同乐”的休闲项目,让我稍微轻松一下。项目之一,就是带我去现场看“四国五强”篮球赛。 已不记得“四国五强”篮球赛是何时开始举办的,但是这一年一度的中、菲、日、韩、四国篮球邀请赛,是当年体坛之年度盛事,“四国”之所谓有“五强”,是因为主办国中华民国有两队参战,它们是“克难”队与“国光”队,通常是由“中广”实况转播(播音)。中广的那位播音员是洪缙曾,在台湾颇有名气,他的口齿相当清晰伶俐,现场转播时,可以让收音机旁的听众“身历其境”,把球赛现况讲得“钜细靡遗”,所以我一甲子后还记得他的大名。 那时电视机尚未普及,当然也还没有我们现在早已司空见惯的电视实况转播,能够在收音机旁竖起耳朵听洪缙曾的精彩“描述”,已经可以让球迷们之肾上腺大量分泌,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现场看球赛。 被父亲带进烟酒公卖局球场后才了解,那挤得满坑满谷的现场“气氛”,确实会让球迷们比较更“投入”些。还记得十分清楚,咱父子俩看完现场球赛的次日,嗓子都因呐吼而有些沙哑,有一次大慨是赛情紧绷,我们也随着现场球迷们声嘶力竭地“加油”,嗓子沙哑到咽口水时都会隐约作痛,但父子俩乐此不疲。 1969年来美国后,我几乎立刻迷上了美式足球,主要是因为美式足球每场皆有实况转播(以各球队之所属城市为准)。但是美式足球也是一样,即使有电视转播,买票在现场看球的动不动就是八万人(以达拉斯的牛仔球馆计)。 或许是不自觉地在延续父亲的“父子同乐”罢,我曾连续十五年,买过四张(全家四口)达拉斯牛仔队的季票(直到两个孩子都离家去读大学后才停止),每每在现场随着在场观众喊得声嘶力竭,只有“如痴如醉”差可比拟呢。 回头来讲“四国五强”篮球赛吧,那些当年家喻户晓的篮球国手们,我居然还记得下面几位之大名,甚至于那些稀奇古怪的绰号,他们是陈祖烈,唐雪舫,李南辉,霍剑平(大象),黄国扬(肠仔),赖连光(骡子),罗继然(铁皮),傅达仁,卢义信(小三),凌镜寰(水牛),与王毅军等。 少为人知的是,众篮球国手中,以陈祖烈之家世最为显赫,他是革命烈士陈英士的族侄,也是国民党CC派掌门人,陈果夫与陈立夫之“幼”堂弟,他们都是同一个辈份的。 其他众多没有被提到的球星们,请你们看到这儿别责怪我,我已到“从心所欲”的年纪,记忆力显着退化,“竭尽所能、竭脑所思”的就只剩下这么几个名字啦。 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常在中央日报的海外版上,看到“篮球国手蒋海平”的字样,经隔洋与父亲证实,这位大个子中锋,果然就是在我们凤山黄埔眷村长大的“海平”。他家与我们有特殊渊源,海平的父亲蒋梦辉,是我父亲于民国二十二年留英返国后,在陆军机械化学校(装甲兵学校之前身)服务,担任战车学生队第一期(简称战一期)总队长时的五十多位学生之一。可无巧不成书,我日后在成功大学就读时,蒋梦辉正好担任成大军训总教官,我就这样成为我父亲的学生之学生(呃,听起来像是在这儿绕口令)。 父亲喜爱看篮球是有渊源的,他在机械化学校任职时,曾以战一期学生们为班底,组成了一支篮球队,自任领队,蒋梦辉就是其中队员之一。这支篮球队曾勇夺当年南京区各陆军部队篮球比赛之冠军,我以前在家中曾见过一张该篮球队之合影照片,大约是1936年所摄,可惜那张照片已不知所终。 读建中那年,我在三军联大的伙房搭伙,但通常是赶不及三军联大饭厅的晚餐开饭时间的,所以伙房都会准备一个便当让我父亲带回宿舍给我。但是在建中开学前的那几天,我的晚餐却是直接到三军联大的饭厅去吃的。 有一天在饭厅吃完晚饭,正伴随父亲缓步走回宿舍,在离宿舍门口只有不到五十公尺处,突然身后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就在我们身旁嘎然停下,一位身着军常服的将官(帽沿有金边,容易辨识)从驾驶座上一跃而下(他显然是自己开车),直接向我们走来。 来人仪容挺拔,威风凛凛,当场踢着腿“砰然”立正,对着我父亲行了个非常标准的军礼(后来才知道那是德式军礼),还扯着喉咙大声嚷着“总队长好”! “总队长好”?奇怪呢,我父亲当时的职称是三军联大的“教育长”。 父亲也不含糊,立刻将手中卷宗交给我拿着,也将皮鞋踢得砰砰响,当场回了他一个标准的“英式”举手礼,就是掌心向外的那款,然后两人居然相视大笑,一付“老朋友”的样子。 父亲嘱咐我先回宿舍,我一面走,一面回头不断地端详他,心想,真是位英俊潇洒的将军! 虽然早已过了办公时间,但见两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后,父亲就坐上那吉普车,往校本部驶去(显然是为公事),约一小时后父亲才坐着同一辆吉普车回来,两人又再演一次那“行礼如仪”,我在宿舍窗后看得清楚,只觉得“滑稽”,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行“英式”举手礼。 原来,那位英挺的将军竟然是蒋纬国,他与我父亲是旧识,两人虽无密切私交,但是在对日抗战之前,同在南京的陆军机械化学校(也就是日后的陆军装甲兵学校之前身)服务,蒋纬国是坦克教官之一,这群教官可不是“普通”军官,他们完全是当年国府选派出去,在英、美、法、德、等各正规军校留学三至五年不等,学成后返国服务的军事留学生组成。我父亲除担任教官外,还被“中国装甲兵之父”徐庭瑶将军(他是机械化学校教育长,职位等同校长,因为当时全国各军事学校之校长衔头皆为蒋委员长)任命为学生队(也就是正规黄埔军校的装甲兵班)兼学员队(已毕业于黄埔之低阶受训军官)的总队长,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蒋纬国会“搞笑”地称呼我父亲为“总队长”之原因吧。 呃,您千万别小看他们学员队的那几位低阶青年军官,二十年之内,这十几位年青学员,都曾先后在台湾担任过国军装甲部队的司令、副司令或师长等要职。 蒋纬国将军于年轻时,曾经留学德国的慕尼黑军校(当时国军中也有不少德国军事顾问),返国后就一直在装甲部队内的各单位服务,陆军机械化学校是其中之一,与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返国军事留学生们(在机械化学校当教官的就有五、六位)都十分熟谙,生活上也“打成一片”,即使不是私下往来的朋友,也算是旧识罢。 附带一提,1963年,也就是我遇到蒋纬国将军的那一年,他正担任与三军联大隔邻的陆军参谋大学校长。后来我也得知父亲与蒋纬国当年为事何而聚首,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与“建中这一年”扯不上边,以后再写罢。 我进入建中后,被编到高三六班,班上约有五十名学生,班导是军训教官李伟纯少校,他是陆军官校25期毕业的,由于他在学时的陆官教育长是我父亲谢肇齐,所以应该算是家父的直接门生吧。 当年各校的电机工程系是甲组(理工医组)最夯的科系之一,所以联考放榜后,班上有两位进入台大电机系,一位去了交大电子工程系,而我们成大电机系居然有三位建中同班同学继续在一起“切磋”了四年。 与我同届的建中其他班级毕业生,除我之外还有六位考进了成功大学电机系,他们分别是黄君杰(十一班)、黄致庸(十一班)、何光庆(十班)、刘旦业(九班)、卢克梁(九班)、与曾广琛(五班),总共是九位。这么一算,我们这一班约五十位同窗(不包括侨生与军方代训生),几乎有百分之二十是建中毕业生呢! 有这么多的建中同班同学,我显然不可能在这匆匆而逝的一甲子时光中,与他们全都保持紧密的联系,下面就简单地介绍几位吧! 刘民治 他是咱们高三六班的班长(连续两学期),大家都知道,班长是班上同学票选出来的,他若是没有人缘,或是欠缺领导能力,八成是选不上的。 记忆中,他好像与我一样,也是眷村子弟。其实我在高雄中学就读时,外省同学之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眷村子弟,原因是高雄是南部的军事重镇,当年的“六十万大军”,少说也有二十多万在当地驻防,凤山、左营、冈山分别是陆海空三军的大本营。而台北市区里就没有那么多的眷村,民治兄与我可能是班上“唯二”的眷村子弟。 眷村子弟从军的不在少数,民治兄成绩虽优异,但志在从军报国,是我们建中那一届毕业生中,被保送到凤山陆军官校(37期)去就读的一位。日后在陆官毕业时名列前茅,被分发到以“慓悍”闻名的海军陆战队服役。 不妨在此爆自己的料,刘民治与我是一道去军医院做体能检验的,因为我也想去报考陆军官校,给父母亲一个“惊喜”。不料体检结果,刘民治体位是甲等,我体重不足(纸片身材),加上近视度数太深,体位遭列为丙等,就此碎了当职业军人的梦。后来我服的兵役是义务役,非志愿役。 离台负笈美国的前几天,民治兄特别向部队请假,专程到我台北的家中来话别,可见我俩交情之笃。日后他在“特战部队”任职,依保密规定不得与国外通信,我俩就这样慢慢地断了联系。 大约十年前,在德州的一场餐会中,遇到已退休的罗文山将军(前联勤总司令罗友伦上将之长子,陆官28期毕业,曾任军团司令等要职),我向他打听刘民治的消息,才得知他曾在罗将军的部队中任过职,可惜在晋升上校官阶后不久,就因病辞世。 卓允中 允中兄与我一样,也是位高三插班生,由省立基隆中学转学来的。由于我俩高度相当(约178公分),所以当依高矮次序排座位时,我们都被排在最后一列,卓允中是我的左邻。 “允中”之名,应该是取自“尚书大禹谟”中的那段“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或是论语里的“允执其中”(在这儿,“厥”与“其”都是含义相通之语助词,意义相通),可见为他命名的家族长辈,必是饱学之士。 允中兄成绩特优,考进了刚在新竹复校的国立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成为新竹交大第一届的毕业生。他日后在硅谷创业有成,是湾区电子业名人之一。 由于我俩是邻座,放学回家时的公车路线也相似(他住士林区,我则住大直区),都必须路经中山北路,所以放学时经常结伴同行,直到必须得要“分道扬镳”的“圆山动物园”站多年后(动物园才迁往木栅),才各自坐不同的公车返家。 平日除了切磋功课之外,我俩还有一个共同的,“不务正业”的怪嗜好,那就是喜欢“远距离”鉴别轿车之厂牌与型号(至少是在四、五十公尺外)。 呃,看倌您看“傻了眼”吗?这又是那门子怪招? 由于放学时校门口排队搭公车有长龙,我俩经常结伴,由学校徒步到两、三公里外的台北火车站去搭公车,沿途闲亟无聊,就以鉴别轿车打发时间。当年在台北市满街跑的,几乎全是美国四大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思勒与AMC)制造的,好几十个不同品牌与型式的轿车,我俩就远远地竞相猜测它们的厂牌与型号,猜中时的满足感,弥补了“跋涉”之辛劳。 也算是“乐此不疲”罢,就有那么一天,连当年最宽广的中山北路也堵车堵得个水泄不通,两人决定由火车站沿中山北路途步到圆山,一路上兴高采烈地以“鉴别轿车”打发时间,走了近两小时,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我俩显然都儍得可以。 十多年前我曾在硅谷见过允中兄一面,两人在一间咖啡店里畅聊往事直至深夜,日后疏于联系,愿老友依然平安无恙。 虞光 虞光是咱们班上的第一名毕业生,也是班上个子最高的(超过180公分)一位,所以他的座位就排在卓允中后面,也算是我的邻座吧,我们三人时常在一起切磋课业,我是三人之中最“笨”的一个,同窗一年受益于他俩良多,特此致谢。 虞光在联考中大放异彩,他的考试总分应该是全国甲组(理工医科)数以万计的考生之前二十名,高到可以进全国各大学的任何理工医科系(他的第一志愿是台大物理系)。后来在举世闻名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研究所深造,毕业后被联合国的某机构招揽,好像就在纽约市的联合国大厦内任职,直到退休。 虞光的尊翁是当时的台湾大学工学院院长,也就是日后的台大校长虞兆中,虞光的成就应当是有“家学渊源”的,不就是中国人口中的那句“龙生龙、凤生凤”吗? 郝晶瑾与王启元 我有幸与他们两位在建中毕业后,又在成功大学同校四年,但已不再同窗(他俩是土木工程系),所以我们在成大的四年中,交往不太密切,但是他俩的一位土木系同班同学罗庆昌,是我在高雄中学时的同班挚友,所以我对郝晶瑾与王启元毕业后的情况略有所知。 在建中时,郝晶瑾的表现不是很特殊,而且好像“外务”多,“坏”点子也不少,记得前段提到过的南昌路那间弹子房吗?我第一次去那儿“消费”,就是郝晶瑾与王启元把我带去的。王启元日后在台湾经营建筑事业有成,郝晶瑾则负笈新大陆。 据老友罗庆昌说,郝晶瑾到了美国后,有如“脱了胎、换了骨”,成为美国的土木工程专家,是名扬异域的工程学院院士与大学教授不说,他还著作等身,除了用英文撰写过许多土木工程的教科书,发表过一篇又一篇的杰出论文之外,也写了不少与他专业无关的著述,以流畅的中文,风趣地谈古论今,可说是文(文学)武(工程专业)全材。 前些日子,成大颁发他“杰出校友奖”,确是名至实归。 可惜的是,郝晶瑾与我俩的共同朋友罗庆昌(比利时土木工程博士、成大土木系资深教授),约于十年前在台病故,感叹声中,又凋谢了一位老友。 赵瑚与周重光 我们班上人材济济,这两位是班上之成绩佼佼者,风风光光地考进大部分甲组理、工科考生们的第一志愿──台大电机系。 他俩虽属同系、同年还又同窗,但日后在电子与电机工业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十足印证了我在“0与1的故事”中所谈及的,这一甲子以来的电子工业革命,衍生了太多的枝枝节节,而且有些电子领域居然还是“互不相属”的。 举例而言,我在北德州有两位同龄的密友,其中一位是曾在成大电机四年同窗的李耀亭兄,他的专业是“红外线二极体”之研制与生产,他的实验室与厂房中那些设备,与我搞自动化与人工智慧的数位工程领域,何止有天壤之别。 还有一位是专精军方“极高频”微波通讯的刘英毅兄(不幸于2020年病逝),他也是我几十年来的“钓友”、“牌友”兼“歌友”,但我俩在湖边、海边,甚至于麻将桌上,卡拉OK银幕前,绝对不会讨论工作上之琐事,因为必然会导致“鸡同鸭讲”。 回头来看赵瑚与周重光的领域吧,赵瑚专精“微电子”,在美学成后返台创业,是新竹工业园区“晶豪”电子公司之创办人。周重光则是美国知名的“电磁波”学者,好像与“医学电子”也有相当的关系,与赵瑚之工作领域则几乎无关。 您看看,以上所写的四百余字,虽然只提到五位电子工程师,就已划分出五个几乎互不相属的电子领域,难怪有些大学已经将电机系提升到与工学院平行的“电机学院”地位,因为电子界的涵盖领域,几已超越其他工学院各系领域之总和。 丘宁世 丘宁世是台湾鼎鼎大名的抗日前辈,丘逢甲之嫡系后裔,也是郝晶瑾的“哥儿们”之一,至于溜去南昌路的弹子房打撞球那桩事,宁世兄堪称是咱们的“领头羊”。 宁世兄大学毕业后,留在台湾办教育,长期担任某私立中学之执行校董,为台湾作育英才,不负其先祖之盛名。 余光湫与叶弘胤 我与他俩缘分颇深,居然同窗长达五年(建中一年,成大电机四年)之久。 成大毕业后,他俩没有出国,在读完国内的电研所后,就如许多成大的工学院毕业生一样,留在台湾打拼。余光湫的“剑扬电子”,与叶弘胤的“台证科技”,都是成大电机毕业生在台湾创业之典型。 根据几十年来的就业纪录显示,台湾企业界与工业界最爱雇用成大各系级之毕业生,不仅因为成大是台湾顶尖学府之一,也因为成大毕业生中,“楚材”被“晋用”之比例(也就是出国深造后,一去不返的留学生们,不幸我也是其中之一),比起其他顶尖学府要低些。 以我们成大电机五十七级的毕业生为例,在国外拿到高等学位后(甚至于是在国外工业界汲取经验后),返国创业的比比皆是。台湾电子业在这二十一世纪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世界级地位,成大电机的毕业生着实功不可没。我就随便举个被各界誉为台湾“护国神山”的“晶圆代工”业为例吧,曾长期担任台积电副董事长的曾繁城(张忠谋之副手,成大电机五十六级),与联电副董事长张崇德(曹兴诚之副手,成大电机五十七级,与我同级),都是长期在“晶圆代工”业奋斗有成的创厂员工之一。 喔,那老张﹝张崇德﹞就更不用说啦,他居然还是我自大二起,在台南的三年同房(Roommate)呢!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同届的一位毕业生,十七班的蒋慕琰,是我在凤山陆军子弟小学(诚正小学)就读时的同班同学,不过我是在几年后偶尔翻阅建中毕业纪念册时,才注意到他的照片与名字。十七班在红楼的西翼,与位于东翼的六班有些距离,而且好像我俩自小学五年级以后就“各奔前程”啦,六、七年后经过青少年时期的“形象演变”,是有可能会相遇而不相识的。 蒋慕琰日后考上台大农艺系,毕业后进入当时相当于行政院农业部的“农复会”,逐步成为颇有国际知名度的台湾农业专家之一,曾数度到美国参访与进修。他还曾担任过中华民国驻非洲尼日共和国的农耕队队长,将台湾的农业技术推广到非洲。 在北德州落脚的建中校友应该也有不少,如今在华裔社交圈中十分活跃的郎德隆(一班)与赵友安(四班),都是与我在建中同届毕业的两位校友,特此一记。 既然在本文之始,引用了校歌中的头两句“东海东,玉山下”,不妨借用校歌中的最后两句“努力奋斗,同建大中华”来收尾罢,这两句歌词也是校方对我们莘莘学子的期许,加上校歌中那“为梁为栋,同支大厦”的字句,明显地是在鼓励毕业生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 自1964年以后,建中毕业生若是以每届一千位计,也该有六万人了,其中在日后出国留学的应该不少,但是像我一般就此终老国外的也比比皆是,我们这些“楚材”遭“晋用”的滞外建中毕业生(当然还有其他各院校毕业后滞外未归的留学生们),不就都成了国家建设的“逃兵”了吗?想起来难免有些汗颜。 套句老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近一甲子的岁月,在弹指间匆匆飞逝,蹉跎的旅外岁月中,我也就这么“白了头”。回首往事,这负笈异乡之背景,虽然确实是有些家庭因素存在,但最后工作地点之决定权还不是在自己吗?留在异乡打拼的这条路,不正是自己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吗? 所以在这夕阳近晚之际,我们这些“过河卒子”,纵使心有遗憾,也只好平淡地把过往的岁月,当作车中后视镜里那飞逝的场景,统统抛诸脑后。记得在三国演义里,作者罗贯中引用杨慎那“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千古名句,不就是想告诉你,人,应该洒脱一些,别误了自己在彤阳美景里该扮演的角色。 特别在此向那些留在台湾(或是旅外学成后返国服务),“努力奋斗,同建大中华”的同学们致敬,你们(尤其是那些与我同行的电子工程师们)的成就,让中华民国的微电子工业,在这二十世纪兴起的全球性电子工业革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至于校歌中那“为梁为栋,同支大厦”的字句,我们就“唐吉诃德”式地把这“大厦”延伸为“世界科技文明”,勉强地自我安慰一下吧。 【美国德州谢行昌,完稿于2021年七月】 相关新闻: 编辑推荐: 热门新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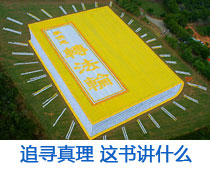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