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翻墙 | 三退 | 诉江 | 中共卖国 | 贪腐淫乱 | 窜改历史 | 党魁画皮 | 中共间谍 | 破坏传统 | 恶贯满盈 | 人权 | 迫害 | 期刊 | 伪火 社论 | 问答 | 剖析 | 两岸比对 | 各国褒奖 | 民众声援 | 难忘记忆 | 海外弘传 | 万人上访 | 平台首页 | 支持 | 真相 | 圣缘 | 神韵 | |
|
【大纪元2016年08月02日讯】暴烈、横行了十年的“文革”全民狂热,从刘少奇、邓小平的角度去看,是一个大灾难;但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发了疯的亿万民众,居然是非常听话的,运动收放自如,从“天下大乱”轻易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我想说的重点。 暴民政治的最大典范,是法国大革命,所谓“雅各宾党人”、罗伯斯皮尔,再加上“断头台”,血迹斑斑,世界震惊。法国大革命弄到大家轮流上“断头台”的地步,革命者们身不由己,彻底的失控,最后只得由拿破仑出来收拾残局,复辟皇权。所以法国大革命砍皇帝的头,备受争议,这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常识。更重要的是,由于法国先贤们的努力,比如雨果的传世之作《九三年》等,使法国大革命成为“普世记忆”,又惊醒历史。然而,从1793年到1966年,一百七十年后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残暴得多的“革命”,却是由一个东方的“皇帝”亲自运筹帷幄的,这大概会让路易十六死不瞑目。所以醉心“群众革命”的西方新左派崇拜毛泽东,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粹主义是暴民政治的温床,它的完成式是最终酿成“现代极权”,即列宁式政党对普罗大众的全能式统治——大众从反抗主体最后沦为奴隶。旧俄知识分子正是从法国雅各宾党人那里接受了民粹主义思潮,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而列宁则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 法国大革命使得“暴民政治”成为可能的研究对象,系统研究成果也出自一个法国人,即大家都熟知的古斯塔夫?勒庞的(GustaveLeBon)《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这篇文字里,我基本上是希望藉用这本书的观点来分析文革这场“民粹运动”。 一、文革群体 勒庞认为,人们为偶然事件或一个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自觉的个性就会消失,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就获得了一种心理群体的特征,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消失、智力下降、感情彻底变化。他具体归纳了五点: (1)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群体不会深思熟虑。 (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总是走极端。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5)群体的道德,有一种净化的倾向,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 把以上五点再浓缩一下,其实就是两点:低智商和受操控。 根据上面这些分析,我认为对文革中的群众行为做过高的评估和赞扬,很难不是偏颇的。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对文革的记忆、研究等,都显示出一种所谓“灯下黑”的局限,或者还有某种身陷其中、不容易撤离出来作工具分析的特征;我们很容易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却无力解构“群众的文革”。其实,我们把“群体心理”这个课题放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亦即1960年代的政治社会思想状况下,不难找到大量的、非常生动的具体事例,去佐证勒庞从法国大革命中归纳出来的那些特征;或者说,文革结束四十年了,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自己的勒庞医生。 假如勒庞有幸遭遇文革,我猜他高度兴趣者,会是“文革群体”特征的成因,这也是我们研究文革时还必须添加的一个因素:前文革的驯化,对于文革群体的基本素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或者说,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已经花了十七年时间来操控、玩弄、虐待中国群众,他才有那么大的自信,敢于发动几亿暴民去摧毁他亲手缔造的这个党和国家机器。 前文革驯化,是个大题目,这里仅列其要点: 镇压与屠杀,造成恐怖氛围,吓阻一切反抗于萌芽状态——五零年代的一系列肃杀行为,如土改、三反五反、按指标杀人、前政权基层骨干一律“杀关管”等,一举震慑民间,从此鸦雀无声,所以才有邓小平“六四”镇压前所谓“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经验之谈,中共将此再施用一次,果然铺垫了二十年经济起飞和权贵阶级的铸成。在这个概念上,中国人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吓破了胆的“群体”,这一点对于“文革群体”和后来的“八九群体”的性格特征,都很重要,恐惧永远伴随着中国的抗命运动,使之易于激进、失控。 用阶级划分,制造大众对“一小撮”的隔离——毛泽东是一个搞“多数人暴政”的大师,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阶级划分的作用,在于从社会中隔离出一个“少数”的另类来,作为整肃和折磨的对象,从而又示范给那个施暴的“大多数”,令施暴他人以释放自身恐惧成为家常便饭,也是文革的一种常态。 反复搞运动,依次在不同阶层之间互换“加害者”与“受害者”——人人成为一个无所顾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个尚有起码常识和秩序的社会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诀窍,其实很简单:他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文革”中入狱近十年的作家张郎郎对此归纳了一个绝妙的观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获得某种心理安全。 用意识形态不断洗脑,以“集体”、“国家”代换“个人”,不止阉割灵魂,连话语也在潜意识中被改造——叫你只能说让你说的话。 …… 所以“文革群体”是在这样的政治前提、思想素质、精神思维语言状态下,走进文革的暴风骤雨中。勒庞用的“乌合之众”一词,带有强烈的心理学意味,用这个词来描述文革中的大众,我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传统意义上已不复存在,因为上层儒家官僚机构、中层乡绅自治、下层宗法家族组织全部瓦解了,而取代它们的中共各级党委、各级政府也全部被摧毁了,这种状况下的民众,跟传统社会瓦解之后的流民、啸聚山林的造反好汉有多大区别呢?如果再加上前面所分析的“驯化”,这样的大众与1793年的法国大众,也即勒庞这本书里归纳的那些特症,又如何对比?也许将来会有人来做这件事。 二、“群众斗群众”是如何挑逗的? 群体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大众”和“领袖”两个问题。勒庞这本书里,关于“领袖”这部分的议论分析并不精彩,只是讲了一些常识,比如他说: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 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勒庞这个分析,倒是很符合毛泽东,疯癫、无情。 他大致上讲了一个规律,领袖分两类:一类是勇猛、实干,另一类是意志力更持久,也更为罕见。 我们都熟知韦伯对政治领袖的一个著名分析,即所谓“奇理斯玛型”领袖,也叫魅力型寡头——他从社会学角度做的这个解剖,确实比勒庞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来得深刻。勒庞也讲群体的幻觉和煽动家对群众的麻醉,但他只讲到领袖人物的所谓“名望”的魔力,就比韦伯的“魅力”低了一个层次。韦伯最精彩的地方,是说魅力乃转瞬即逝,不能反复使用;而且大众有一种对魅力的渴望和上瘾,这恰是领袖的致命之处——他最终会为了维持魅力而毁掉自己。这个论述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几乎可以从中西方古代的那些“英雄豪杰”,一直涵盖到近现代的枭雄,如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等,当然毛泽东也逃不过这个罩门。 毛泽东有“造神”的自觉,特别擅长勾引追随者为他“造神”,前有刘少奇,后有林彪;有趣又在,“文革”简而言之,就是毛泽东利用第二个“造神者”去摧毁第一个“造神者”;也因此,当第二个“造神者”坠毁温都尔汗之际,那把大火也顺便把毛泽东这座神像焚毁了。这些在今天都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因为毛泽东至今还是中共的神主牌,他并没有遭到任何程度的解构,尤其他操弄大众至疯癫境地的这场文革,可谓他的登峰造极,对世界与中国至今仍是一头雾水。文革既是毛泽东的一个神话,也是解构他的一把钥匙,其中最有魅力的问题,是他操弄大众的伎俩,是不是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有待分析。勒庞也分析领袖的“统治手段”,比如他说“掌握了影响群众想像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这在毛泽东身上怎么表现的,是个好题目,但不容易分析。我觉得可以很容易看到的,有两点: 1、“两报一刊”指挥 毛泽东不过是使用了自己的几个秘书——连江青在此的身份角色不是毛妻而是一个秘书,再加上几个文痞,就指挥了这场文革,其指挥、控制的手段,仅仅是通过党煤(中国只有党煤)发社论,或颁发文件(另一个辅助手段就是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召集各地各派别代表谈判),几乎谈不上任何“想像力”,就是枯燥的文字命令而已,像军事命令一样畅通无阻到全国的所有角落,遇到抗命或阳奉阴违的情形也很罕见,八亿人和偌大一个神州被毛泽东指挥得圈圈转,这在人类历史上至少是空前的。 文革从“一张大字报”的发动,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收盘,全靠社论指挥,仅举几例即可: 文革的第一场较量,就是围绕姚文元一篇文章展开的,即所谓“舆论指挥”权的争夺,刘少奇一派便以损失“彭罗陆杨”四员大将而败下阵来。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向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私下组织。彭真、陆定一抵制转载此文,毛在上海还曾下令印刷小册子,由新华书店系统发行;而《人民日报》迟至11月30日才在《学术研究》版内转载此文,两端激烈争夺,而就在此文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罪名,被撤销中办主任之职;林彪也开始动手整肃总长罗瑞卿。自1962“七千人大会”后到65年这段期间,毛有部署地展开对文艺、学术的批判,如对戏剧《李慧良》、《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学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学界批杨献珍、经济学界批孙冶方等,此乃所谓“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来,因为毛觉得“大权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帮秘书来发动反击。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文革动员手段,但此举必须配合一个口号的传播,方能凑效。文革研究者何蜀曾分析过“造反有理”这句口号的出笼,也是有趣的一例。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公开引用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的语录,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话是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说的,1949年12月20日新华社重新引用过,但后来并没有被编入《毛泽东选集》。27年后《人民日报》或许是不经意援引它,却令红卫兵们如获至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连写“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又经江青转递给毛泽东,再由《红旗》杂志第十一期以“革命小将的大字报”为题公开发表、配发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人民日报》转载这三张大字报,连续几天反复刊登这段“造反有理”语录,中央乐团奉命将其谱成歌曲,从1966年国庆节前夕开始,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全国传唱。 红卫兵一大血案,是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们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13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该女子中学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一只红卫兵袖章,而毛泽东听说宋的名字是“彬彬”时说:“要武嘛。”这是整个文革中直接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一次最赤裸扩的暴力诠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同时,这个瞬间也变成媒体传播、宣示暴力指令的生动样板。《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导。据王友琴调查,8月18日后北京校园暴力和杀戮全面展开,仅西城区8月下旬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61所中学平均每所中学打死五个半人。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不仅北京,1966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杀人场。 这里的含义是,不使用“枪杆子”——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手段,只靠它的威慑作用,毛泽东可以仅仅用秘书——在中共语汇里即“笔杆子”,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暴民运动,摧毁整个政府、国家机器和整个列宁式政党,这不仅在政治学上是一个大题目,恐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大题目。从常识看,在任何制度建制下,从皇帝到现代独裁者,不依靠官僚阶层(即所谓“科层制”),是不可能对社会作起码的控制和运作,仅仅靠“意识形态命令”(两报一刊社论)指挥文革十年,其机制至今是一个谜。 2、军管 毛泽东并非不使用“枪杆子”,从使用“军代表”开始,便意味着他是靠“枪杆子”收盘的,表面上的说法叫着“大联合”、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这些步骤都是在“军代表”的看不见的枪口下完成的。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然而,这个可以称为“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却是文革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整肃、虐待、枪杀、监禁最惨烈的时期。毛泽东除了五〇年代初期,曾滥施警察、军队等镇压工具之外,文革中“军管”是最赤裸裸的一次施暴,比如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开膛破腹,就是一个军代表实施的私刑,惨烈程度超过六六年的“红八月”暴行。 然而,毛泽东的“军管”又很特殊,跟世界上许多“军政府”都不一样,也不是中共原有的那一套话语(“党指挥枪”)可以描述的。在文革这个题目下,至少可以有几个研究点: ——毛泽东达到清洗刘少奇的目的,就想恢复政府功能、“抓革命促生产”,回到常规,但文革闹到“全国内战”的程度,已经失控,他的权威也受到挑战,比如1967年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他几乎是仓皇逃离,所以他不得不打出他的最后一张牌“军管”。文革收盘用军队,就是强制性恢复秩序、收缴权力、结束“民粹运动”,毛很清楚这是不可能靠“笔杆子”发社论就能办到的。事实上“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在各省市都经历了一场剧烈派性纷争、武斗、人头落地、充满阴谋的过程——毛赖以发动文革的魅力也随之消耗,这都极符合韦伯的说法。 ——毛泽东其实并无失权之虞,他靠林彪“保驾护航”,是把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变成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因此“军代表”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六十年代中国的一场现代迷信,达到全民共谋迫害“异教徒”的程度,内幕也极其血腥,至今只露出冰山一角。 ——放纵群众、煽动民粹,都是需要支付代价的,法国雅各宾党人的命运终于也落到毛泽东头上——他靠军管收拾残局,却又不肯分权于林彪(设国家主席),终于引发“副统帅逃亡”的重大危机,也导致毛的“天纵英明”一夜尽失。文革灾难,林彪是毛泽东的第一帮凶,他的作用远甚于“四人帮”,当下民间盛行的“林彪冤案”是一个伪问题。 三、“民粹主义”流变 共产党这个东西,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它没有多少办法——为了公平、理想而滥施残暴、反人道,很难说得通。民粹主义衍生成“不择手段”,被解释为苏联专制的根源,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来自《斯大林秘闻》一书。 此书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是史学家,也是剧作家,曾花二十五年创作《末代沙皇》,畅销世界。《秘闻》认为前苏联的悲剧并不能简单归之于斯大林的暴君和独裁者性格。与其说是斯大林缔造了苏联历史,还不如说是苏共在十月革命前夕争夺、巩固政权中需要这样一位残暴的领袖。 俄国知识分子和青年贵族,受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的影响,接受民粹主义思潮,成为“十月革命”和列宁式政党的思想来源。民粹主义有三个要点:一是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二是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三是主张利用农奴服从成性的弱点,强迫他们走进新社会,甚至主张彻底消灭这个阶层。 列宁式政党将这三点完全继承下来。尤其,列宁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斯大林作为他的接班人,对“不择手段”尤其心领神会,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用于对付沙皇政府,也用在对付党内同志,发生包括“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营”在内的七十年罕见暴政,有研究发现,其惨烈后果包括导致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下。 无疑,“民粹主义”三要点也是被中共完全继承下来的,但毛泽东放胆玩弄“大规模群众”如文革这类把戏,则是苏共不敢望其项背者。毛泽东是一个搞“多数人暴政”的老手,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如前所述,他的诀窍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多数”能够为广泛的过激行为提供“理由”,就是民粹主义,但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以更大的权威来恢复秩序,这是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仑专制的道理。中国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别,最高权威毛泽东不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权威始终没有被怀疑过,以至社会的法纪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沦丧的境地。 “多数人的暴政”在中国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施暴者”行为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又如在广西发生大量吃人暴行,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了?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人相食”了。这才是“文革”研究的最大挑战。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初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 还有一点。文革和八九学运,两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两者最后的制度化结果,并未对民间社会存留什么积极的遗产,反而是刺激了中共体制处理“民粹运动”的马基雅维利技术。八九学运有意无意间在模仿文革,或者说,文革中的许多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遗传到八九学运中来;而中共当局最初定性学运和最终选择调野战军进京镇压的决策,其潜意识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文革经验”。 我们现在面对和承受的现实是,“六四”镇压后,中共建构钢性“维稳”系统,返回“全能主义”控制,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民间的任何意愿,并成功达至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高腐败的“经济起飞”,得以配合跨国资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种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中国模式”,虽然这二十年间国际社会接连发生了“苏东波”共产体制坍塌、中东“茉莉花”民间抗议风潮两大成功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国的经验解构了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必定促进政治进步”的预期,提供了关于“公民抗命”的相反实践。中国在一个极短促历史中的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竟然走向彻底相反的结论,这是非常讽刺的。 --原载民主中国 责任编辑:方凡 相关新闻: 编辑推荐: 热门新闻: 下载翻墙软件浏览原文:苏晓康:中国的乌合大众——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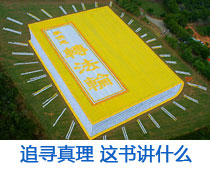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