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翻墙 | 三退 | 诉江 | 中共卖国 | 贪腐淫乱 | 窜改历史 | 党魁画皮 | 中共间谍 | 破坏传统 | 恶贯满盈 | 人权 | 迫害 | 期刊 | 伪火 社论 | 问答 | 剖析 | 两岸比对 | 各国褒奖 | 民众声援 | 难忘记忆 | 海外弘传 | 万人上访 | 平台首页 | 支持 | 真相 | 圣缘 | 神韵 | |

一、老绒树下的小男孩 多余是我的小学同学,年长我三岁。高高的个子,长得白白胖胖,脸庞也方方正正的,很老实。但老实得过头了,就显得有些木讷,呆头呆脑。他脑子不太灵光,所以学习很差,总是留级,最后竟与我成了同学。 他是我奶奶家西北角的邻居。他家的门前有三棵高大的绒花树。夏天,每当绒花盛开的时候,空气里满是那特有的清香,淡粉色的花苞像圆圆的小绒球,开展了又像一把精美的折扇,娇艳美丽,而又素雅清淡。纤细似羽的叶子日落而合,日出而开,甚是灵性,人们叫它合欢树,我特别喜欢。所以每当绒花盛开的时候,我总是跑到他家门前去捡凋零的绒花玩。 多余的母亲早早的过世了,大哥也已成家另过。姐姐也嫁给了南边村里的在县公安局工作的一个小头目。现在家里只剩下他和尚未成家的二哥与父亲生活。 他不大爱说话。看不见他与别的男孩子玩,也许是因为学习不好而自卑的缘故吧。很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他也常常被别的男孩子们欺负。而偌大个子的他也从未见还过手。我在他家门口玩,而他也很少与我搭话,只是蹲在大门洞里,静静地看着我们玩。 大绒树的东边有一棵高大的老槐树,枝繁叶茂,浓密的叶子遮蔽了阳光,那里是夏天乘凉的好去处。大槐树上有一个硕大的马蜂窝。不过马蜂素日你不惹它,它也不蜇人。 大槐树下有一堵矮矮的土墙头,墙头的里面是村民秋天储存红薯的地窖和冬天老太太们纺棉花的地荫子。土墙的背阴处总是长着厚厚的碧绿青苔,特别是雨后,更多、更绿。我捡完绒花,就待在槐树下玩会儿绒花,再玩会儿青苔,有时也和小女孩们玩抓石子,跳“房子”、跳绳、摔纸叠的元宝等游戏,天天乐此不疲。既便有时是我一个人,也玩得很快乐、很惬意。那里是我儿时的乐园。 村里的男孩子们有些是很顽皮的,有时淘气起来也是无法无天,不分轻重。 那是夏日的一个中午,我又独自在槐树下玩绒花,几个坏小子跑过来,趁我不注意,悄悄地捡了几个石子,狠狠地向树上的马蜂窝掷去。马蜂窝被击中了,愤怒的马蜂,乱成一团,四处寻找着报复的目标。 干了坏事的坏小子们见此,嗖的一下四散逃跑了,只有毫不知情的我成了愤怒的马蜂攻击的目标。 立刻我的头上、脸上、身上被马蜂蜇了好几个包,很快整个头脸就肿得面目皆非了。站在门洞里的多余惶恐地辩解着:“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并很快地向我家方向跑去。 一会爷爷来了,将被马蜂蜇得面目皆非的我领回了家。 大概是在三年级春天的时候,我们正在课堂上静静地听老师讲课,忽然教室的门被推开了,校长、村支书、民兵干部、还有几个不认识的陌生面孔,阴沉着脸鱼贯进入了教室,气氛紧张、严肃,如临大敌。我们忐忑不安地瞅着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校长将一张张的白纸条发给大家,并严肃地说:“同学们,请大家答一份卷子,默写: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签上自己的姓名,交上来!”学生们在紧张的气忿中,小心翼翼、忐忑不安地写好了纸条,校长一一收好。随后,一行人又到别的年级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学校里出了大事:原来是在学校的后墙上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这在当时的把毛泽东奉为神灵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环境下,这可是天大的罪行,被抓住就是“现行反革命”,让我们写纸条的目的就是为了核对笔迹查罪犯。当时这事一经发现就被报到了大队、公社、甚至县公安局,他们都派人来当作一件大案、要案调查了。母亲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教师,只是没教我们班。所以才了解了一些这事的详情。那时全校甚至是全村所有的人都非常惶恐,生怕会飞来无端的牢狱之灾,降临在自己身上。 经过好几天的筛查、核对笔迹,罪犯终于查到了,反动标语竟然是多余写的。所有的人终于松了口气,将悬着的心放下了。而多余的家却像塌了天。幸亏多余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姐夫多方打点、周旋,总算以多余是傻子智力有问题为借口,才将此事平息了。而多余的结局是再也不能继续上学读书了。 但这条标语究竟是不是多余写的,没人知道,我也没有问过他,终究也不得而知。  夏天,每当绒花盛开的时候,空气里满是那特有的清香,淡粉色的花苞像圆圆的小绒球,纤细似羽的叶子日落而合,日出而开,甚是灵性,人们叫它合欢树,我特别喜欢。(Shutterstock) 夏天,每当绒花盛开的时候,空气里满是那特有的清香,淡粉色的花苞像圆圆的小绒球,纤细似羽的叶子日落而合,日出而开,甚是灵性,人们叫它合欢树,我特别喜欢。(Shutterstock)
二、马老根 后来我们家盖了新房子,我们便离开村子中心的旧房子,搬到新房子里住了。 新家就在村东口,门前是通向邻村的大路。东边是刚盖的新房尚未住人。西边的邻居是母亲儿时的好友兼同学,她也是我中学的老师,我一直称她琴姨。南面隔街则是一户地主。 地主的名字就叫马老根。是一个白白胖胖(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闹病而导致的浑身浮肿)长得慈眉善目的六七十岁的老头。他膝下没子,现在的老伴是后娶的,有一个女儿也是后老伴带过来的。 他长年带一顶黑色瓜皮小帽,着一袭黑色洋布裤褂,拄一根拐棍,提一马扎,常坐在房后歇息。 他家也是典型的农村四合院,但临街房和西厢房都在土地改革时被中共邪党给拆分了,连院墙也没有了。从他家门前路过,他家的一切一目了然。从青石板铺就的院子和残存的东厢房和正房的建筑规模依旧能看出昔日繁华的影子,在东厢房的窗下有一株鲜花盛开的桃树。 老人很孤独,也很寂寞。因为成分高,不断被批斗的缘故,村里没有几人与他说话、唠嗑。他的西邻是他先前账房先生的儿子,据说还是同宗族。但每见了他也是横眉冷对、高声斥骂。他每次都是默默地承受,一声不吭。就连他的后老伴对他也是冷冰冰的。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墙根下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他与姥爷是老相识,所以母亲对他很尊敬,见面总叫他叔,也让我称呼他爷爷。所以他对我很好,见了我也很亲切。也许是太寂寞了,每次见了我总是他先招呼我,有时也讲故事与我听。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大意是一个后母虐待继女,让她在寒冬腊月里出去采摘鲜花,摘不回来就不让她回家。后来继女在神仙的帮助下,采回了鲜花。而恶毒的继母和她同样坏心眼的女儿则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然而我毕竟生活在共产邪党的天下,耳闻目睹的全是共产党的歪理邪说,从小被灌输、与洗脑的都是谎言、暴力、血腥与欺骗。天天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都是地主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的滔天罪行。而老根爷也是地主。渐渐的在我的脑海里他也和老师讲的凶狠、残暴、剥削长工的刘文彩们融为一体。我开始躲避他了,慢慢的与他越来越疏远了。他只能远远地默默地看着我。 后来在墙根下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了——他病得已经不能出门了。 初中的时候,学校给我们布置了一个政治任务: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揭发地、富、反、坏、右宣传迷信、破坏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我从小到大在学校都是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事事都是走在前面。于是,我把老根爷给我们讲故事宣扬迷信的事报告了我的班主任——琴姨。琴姨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没往上汇报。 过了不久,老根爷就在孤独寂寞中病故了。他死得很凄凉、葬礼也极为简单。 很多年后,我给孩子买童话书,看到了安徒生的童话,我才知道了老根爷给我讲的童话故事的出处。我才知道我在初中时干了一件多么愚蠢而可耻的事,我深深的为自己无知的行为羞愧,我出卖了一个善良的灵魂。然而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谁之罪?!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转眼间,老根爷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的坟冢也早被夷为平地。然而我心底的罪恶感却一直不能消除。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宽恕我的无知与愚昧,我希望他能转生在一个没有共产邪党的社会里,能幸福快乐的生活。  秋风凄凄,寒蛩低泣,周围只有不知名的野花在风中摇曳着,陪伴着她那孤苦和饱受屈辱的灵魂……(Shutterstock) 秋风凄凄,寒蛩低泣,周围只有不知名的野花在风中摇曳着,陪伴着她那孤苦和饱受屈辱的灵魂……(Shutterstock)
三、“怀孕”的女孩 我们村是个小村,左右相邻的两个村子也不大,所以三个村的孩子们上初中就合并在一起,都在我们村的学校里上。那时小学是五年制,初中是两年,高中是两年半。小学一至五年级的学生都是本村的,一个年级一个班,初中是两个班,生源就是三个村的学生。那时小学和初中都在一个校园里,无论开会和做体操也同在一起。所以在课外活动中都能见面。也都能知晓彼此的姓名。那时的初中生也就是十三、四岁的年龄,但在我们这些小学生的眼睛里也都是大哥哥、大姐姐了。 我在读小学四年级那年,初中有个女生,是西邻村的,中等个,微胖的身材,梳着两根大辫子,长得很甜美也挺清秀。忽然有一段时间,风言风语的传说她怀孕了,因为她的小腹部位明显的凸了出来,后来竟越来越大。未婚先孕,这在当时的农村,传统道德还没全毁,社会风气还没堕落到现在这种程度下,这种事情在乡下都是伤风败俗和为人所不齿的。一时间这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这个女孩的身影就从校园里消失了,是被学校开除了,还是自己弃学不上了,不得而知。 后来在课间活动时断断续续的从她同村的学生们的口中得到了她的一点消息:她被村里大队干部和民兵们关押在大队部里,逼问、拷打,让她供出“奸夫”是谁,女孩开始一脸茫然 ,紧接着只是哭,后来受刑不过,便胡乱说出了一个同村的男子。男子平白无故的担了个污名,气愤不过,跑女孩家里大吵大闹,这桩丑事简直在村里闹翻了天。女孩的父母都羞以见人。后来有一天,这个女孩突然间昏了过去。村里的赤脚医生检查不出所以然。送到公社卫生院,也查不出病因,最后转县医院,才查出女孩是得了绝症,腹部凸出是因为腹水引起的。人们这才知道是冤枉了女孩。但没有任何人去为这件事承担责任。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女孩就病故了。因为是未成年,家人只是给她买了口薄薄的棺材,简单地装殓了她的尸骨,将她葬在了乱坟岗上。 秋风凄凄,寒蛩低泣,周围只有不知名的野花在风中摇曳着,陪伴着她那孤苦和饱受屈辱的灵魂…… @* 责任编辑:林芳宇 相关新闻:编辑推荐: 本文转自大纪元(国内需用翻墙软件才能访问) 手机上长按并复制下面二维码分享本文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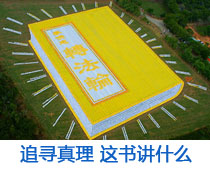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