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翻墙 | 三退 | 诉江 | 中共卖国 | 贪腐淫乱 | 窜改历史 | 党魁画皮 | 中共间谍 | 破坏传统 | 恶贯满盈 | 人权 | 迫害 | 期刊 | 伪火 社论 | 问答 | 剖析 | 两岸比对 | 各国褒奖 | 民众声援 | 难忘记忆 | 海外弘传 | 万人上访 | 平台首页 | 支持 | 真相 | 圣缘 | 神韵 | |

测量失智与否有个通用的量表,称为长谷川式失智症量表(Hasegawa Dementia Scale),不仅日本,台湾也采用。在诊断失智困难的年代,是全世界第一个可以短时间筛检失智的简易量表。 发明者长谷川和夫医师研究失智与临床工作接近半世纪。二○一七年,他罹患失智,二○二一年离世。二○一九年底,他以失智症者的第一人称,向世界发言。在这任何人都可能失智的时代,长谷川和夫提出研究者眼中的失智,与实际失智后的差距,以及疾病背后的勇气、希望与庄严。 以下是长谷川和夫出版的《我终于了解失智了,失智专科医师失智后向日本人说的遗言》,以及接受媒体采访的部分内容。 我罹患的是嗜银颗粒性失智症(argyrophilic grain dementia),这是一种八十岁以上才会发病的失智症。我平常看的医师有次突然建议我去看失智专科,虽然我儿子也是精神科医师,他对我的诊断是阿兹海默症,但大家不太相信,后来我去看了附近认识的专科医师,照了电脑断层、核磁共振,也做了测验后,才确诊是嗜银颗粒性失智症。 因为测量失智的量表是我发明的,所以得很高分,医院是用特别的心理量表才确诊。 发病的时间并不清楚,但具体来说,就是对自己的经验变得不确定。 例如锁门后出门,会一直想到底锁了没? 一般人正常的反应是,想一想应该是锁上了,就放心出门了;或是回家确认是否锁上,然后再出门。 但我的状况是,即使已经回家确认过,还是始终不能确定是否真的锁门了。这种确定过的事却还是不确定,又常常忘掉和别人的约定,以自己长年的行医经验判断,应该不是健忘,而是失智了。 在一场小型演讲里,我以专家身份受邀,主办单位希望我给病人家属照顾上的建议,我一开头说:“我这样说也许会给主办单位困扰,但我也失智了。” 失智并不会失去身为“人”的身份,在这长寿时代,谁都可能失智,我从心底想表达的是,即使失智了,依旧可以过着一般人的生活,而且我以身作则地出席演讲。 很多人听到我失智,都很震惊,因为我曾任大学的学务长、理事长,也不曾远离临床工作。二○○六年离开大学理事长的工作后,一直在儿子开设的诊所看诊。 有一天,一个男性来就医,声明是为了确认别的医生诊断,寻求第二意见而来。他的家属说,他最近症状恶化,在下雪的日子跑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由附近邻居发现送了回来。 一开始,他便转向我问:“为什么我会得阿兹海默症,别人不会?” 我当然可以回答,阿兹海默症是大脑里β类淀粉沉积,但他的表情认真,仿佛从身体渗出悲伤。 如果你是医师,你会怎么回答? 我答不出来。 这时,我知道任何安慰都没有用,说什么只会加深他的痛苦和悲伤,与其说“就算得病了,身为人的本质不变”,我只有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持续握着他的手。 他在公司位居高位,“为什么是我? 我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为社会奉献到现在却得这种病?”当时他强烈的情绪也震撼了我。 回到我失智这件事。年纪大了,得到失智也没办法,说不震惊是骗人的,但比较多的想法是,我年纪那么大,那是当然的啊。 当然也曾沮丧,想起以前圣玛丽亚医科大学的学长说,“你不是你的疾病,你也不是你的研究”,但现在我可以说“我就是我的研究”。 也有人问,一位名医失智,有些人会选择隐瞒,为什么你选择要公开? 因为我希望人们对失智有正确的认识,失智病人过着伤心、痛苦、令人不耐烦的每一天,希望大众能更懂得面对失智症病人。 如果能对失智症病人说,“没关系,放心,我们都在”,失智病人会安心得多。而且,不只是守望失智病人,更是靠近失智症病人一点,一起往下走,会带给失智病人勇气。 如果问我为什么要公开? 我是为了要让自己活得更好,也就是在我生活的社会与人群,对失智更友善,我希望能为此出点力。 虽然医界对失智的理解愈来愈多,但被诊断为失智的人依旧被视为“那一边”的人。“这边的人”以为“那边的人”无法对话,什么都不懂,轻易地说出伤害人格的话。 失智症的人懂,不管是说他坏话,把他当笨蛋,那些被嫌恶的感受依旧会留在他心里,虽然他可能什么都没说,但他知道。 被无视、被轻蔑,这些悲伤或痛苦是我们变成大人的过程中,在职场或家庭或多或少都遭遇过,只是失智后,会一再发生。 决定事情时,不要把我们排除在外,不要把我们放在一旁。 和失智病人接触时,一定要留心,把他当作对话的对象,不要妄自帮他决定该做什么。反而可以问,“今天想做什么”或是“今天不想做什么?” 即使有些人失智后,真的什么都不懂了,但心还活着,被赞美还是会高兴,被嫌恶还是会受伤,要把失智病人当作和自己一样,是一个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我的经验到底能不能对社会发挥作用尚不可知,但我希望能如实传达失智,这是我活下去的道路。 (网站专文、禁止转载)  书封。(天下杂志提供) 书封。(天下杂志提供)
(本文摘编自《慢老2.0:不是活得更老,而是延长健康中年! 全面升级健脑、强肌、抗衰的日常习惯》,天下杂志)责任编辑:王晓明 相关新闻:编辑推荐: 本文转自大纪元(国内需用翻墙软件才能访问) 下载翻墙软件浏览原文:权威失智医师失智后教我们的事 手机上长按并复制下面二维码分享本文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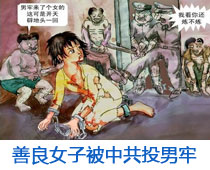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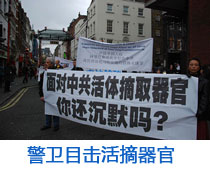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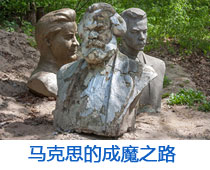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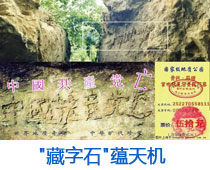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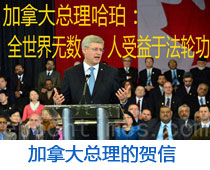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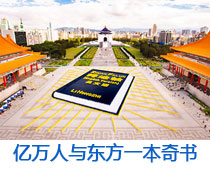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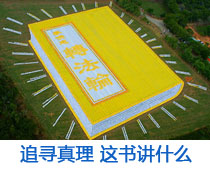  |